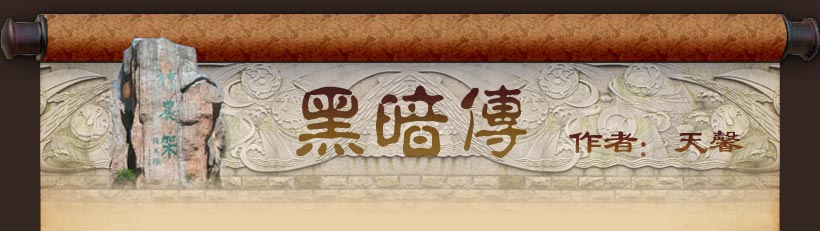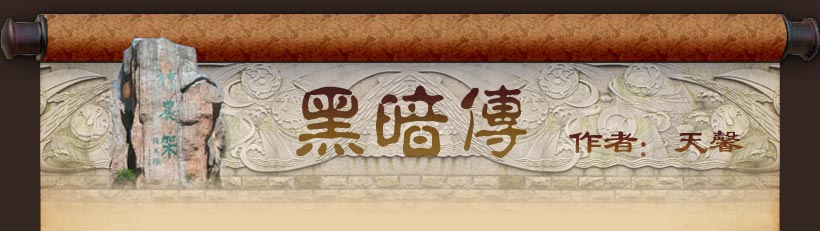|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全面的、长期的,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巨大推动和变化。佛教典籍中如《维摩经》、《法华经》、《楞严经》和《百喻经》 等,本身也是瑰丽多彩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佛教典籍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并为后来的古典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 《红楼梦》等的创作提供了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佛教的俗讲、变文,也直接推动了后来的平话、宝卷、弹词、鼓词、戏曲等通俗文学艺术的形成。佛教禅宗语录也对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发生影响。
佛教不仅对我国古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如佛教的“言语道断”说、“顿悟”说、“妙悟”说、“现量”说和“境界”说,以及“以禅喻诗”,用禅宗的一套禅理来论述诗的创作、欣赏和评论,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可以说,没有佛教的影响,中国汉代以后的古代文学将是另一番面貌。
仅就佛教之禅宗对文学的深远影响,评说一二,亦足见佛光普照之下,中国文学于精彩之外又得以更添异彩。
在中国生根兴盛的禅宗,自初唐开始,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洪流,奔腾澎湃,普遍深入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在有形无形之间,或正或反,随时随处,灌溉之,滋润之。
(1) 诗:从唐诗风格的转变来说:由初唐开始,从上官体(上官仪)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经武后时代的沈(人全)期、杜审言、宋之问等,所谓“景龙文学”,还有隋文学的余波荡漾,与初唐新开质朴风气。后来一变为开元、天宝的文学,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到韦应物、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等人,便很明显的加入佛与禅道的成分。再变为元和、长庆间的诗体,足为代表一代风恪,领导风尚的,如浅近的白居易、风流靡艳的元稹,以及孟郊、贾岛、张籍、姚合。乃至晚唐文学如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等等,无一不出入于佛、道之间,而且都沾上禅味,才能开创出唐诗文学特有芬芳的气息,与隽永无穷的韵味。至于方外高僧的作品,在唐诗的文学传统中,虽然算是例外,大体不被正统诗家所追认,但的确自有它独立价值的存在。受禅宗意境影响的诗文学,到了宋代,更为明显,宋初著名的诗僧九人,世称九僧的风格(如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简长、青城惟凤、江东宇昭、峨媚怀古、淮南惠崇。)影响所及,便使醉心禅学的诗人,如杨大年(亿)等人,形成有名的西昆体。名士如苏东坡、王荆公、黄山谷等人,无一不受禅宗思想的薰陶,乃有清华绝俗的作品。南渡以后,陆(放翁)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四大家,都与佛禅思想结有不解之缘,现稍举一二,宋道济(俗称济颠和尚)的诗: 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倒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
王安石的诗:《梦》: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
范成大的诗:《请息斋书事》:覆雨翻云转手成,纷纷轻薄可伶生!天无寒暑无时令,人不炎凉不世情,栩栩算来俱蝶梦,喈喈能有几鸡鸣?
寒山大士: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慧文禅师:五十五年梦幻身,东西南北孰为亲,白云散尽千山外。万里秋空片月新。
此外,明代禅宗诗僧的作品,诗律最精,而禅境与诗境最佳的,无如郁堂掸师的《山居诗》,如:即今休去便休去,何事却求身后名,世乱孙吴谋略展,才高屈贾是菲生,沟中断木千年恨,海上乘槎万里情,谁识枯禅凉夜月,松根一片石床平。
(2)词曲:自晚唐开始,历五代而宋、元、明、清之间,许多词曲,禅境很好,我们现在简单的举出历来被人所推崇公认的词人曲家作品,以供参考。
如辛稼轩的词:《有感》:出处从来自不齐,后军方载太公归,谁知寂寞空山里,却有高人赋采薇。黄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时,蜂儿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间自在飞。
元曲如刘秉忠的:《干荷叶》,千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又如盍西村的:《小桃红(杂咏)》: 古今荣辱转头空,都是相搬弄,我道虚名不中用,劝英雄,眼前祸患休多种,秦宫汉冢,乌江云梦,依旧起秋风。
清初有名的少年词人,也便是满清贵族才子的纳兰性德的词:《浣纱溪》:败叶填溪水已冰,夕阳犹照短长亭,行来废寺失题名;驻马客临碑上字,闻鸡人拂佛前灯,劳劳尘世几时醒。
(3) 小说:由唐人笔记小说与佛经变文开始,到了宋、元之间的戏曲,以及明、清时代的说部与散记等等,大多是含有佛、道思想的光辉,值得特别注意的,无论是小说与戏剧,它的终场结尾,或为喜剧,或为悲剧,或是滑稽剧,必然循着一个固有的道德规律去布局与收煞:那便是佛家与道家思想综合的观念、人生世事的因果报应的定律。元、明之间,历史小说的创作者都以禅入文,如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开端,开宗明义,便首先用一首《西江月》的词,作为他对历史因果循环的总评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清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依佛学的立场而讲,罗贯中的这一首词,便是《金刚般若经》上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施耐庵的名著《水游传》,只从表面看来,好像仅是一部表现宋、明时代官民之争的作品,如果再加深入,仔细的研究,它在另一面,仍然没有离开善恶因果的中心思想,隐约显现强梁者不得其好死的果报观念。至于《西游记》、《封神榜》等书,全般都是佛、道思想,更不在话下。此外,如历史小说的《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等,无一不含容有佛学禅宗不昧因果的中心思想。由此发展到了清代,以笔记文学扬名的蒲松龄,所着《聊斋志异》,几乎全盘用狐鬼神人之间的故事,衬托善恶果报的关系。《醒世姻缘》一书,更是佛家三世因果观念的杰作,说明人生男女夫妇间的烦恼与痛苦,这种观念,后世已经普及民间社会。至于闻名世界,以长篇言情小说,反映老式文化中贵族大家庭生活的《红楼梦》一书,它的开端,便以一僧一道出场,各自歌唱一段警醒尘世的警语与禅机,然后又以仙凡之间的一块顽石,与一“小草剧伶唯独活,人间离恨不留行”的故事,说明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缠绵反侧的痴情恩怨,都记在一本似真如幻的太虚幻境的账薄上,隔着茫茫苦海,放在彼岸的那边,极力衬托出梦幻空花,回头是岸的禅境。作者在开始的自白中,便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及“假作真时真 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警句,这岂不是《楞严经》上,“纯想即飞,纯情即堕”,以及“主因识有,灭从色除”的最好说明吗?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佛性突破了性别、身份、阶级、种族甚至人和动植物、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界限,在各种人、物身上显现:
有小户人家的女儿,如《清平山堂话本•花灯较莲女成佛记》中张待诏的女儿莲女,她拦住能仁寺惠光禅师问:“龙女八岁,献宝珠,得成佛道;奴今七岁,无宝珠,得成佛否?”龙女成佛的故事出自《妙法莲华经》,这是小乘教义向大乘教义过渡的一个标志。
有忠臣。《说岳全传》中的岳飞,据说他本来是如来佛法座上面的大鹏金翅鸟。
有醇儒。文天祥以养浩然之气自负,但全祖望《梅花岭记》说他以悟大光明法而得解脱。还有皇帝。李玉《千钟禄》写明惠帝仓惶弃宫出走,唱出了千古名句:“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将封建朝代的兴亡概括于佛教哲学,深刻,悲凉。
还有老虎。萧梁王琰《冥祥记》记天竺沙门耆域前行,“有两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头,虎便入草”,是老虎有佛性。
还有蛇。《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记许多蛇“皆有佛性,逢人不伤,见物不害”。
有猿猴。张读《宣室志》记杨叟之子宗肃在山中见一胡僧,自称袁氏,好浮图氏,为宗肃谈《金刚经》,原是猿所化。敦煌变文《四兽因缘》说“弥猴即是大目乾连”,“后得成佛”。
甚至还有石头。长篇小说《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所记的就是一块石头,但不是寻常的石头,而是一块“灵性已通”,“幻形入世”,“引登彼岸”的一块石头,实际上是块有佛性的石头。《石头记》的书名如勉译为现代汉语,那就是:一块有佛性的石头在现实的社会中经历重重磨难而终于皈依空门的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