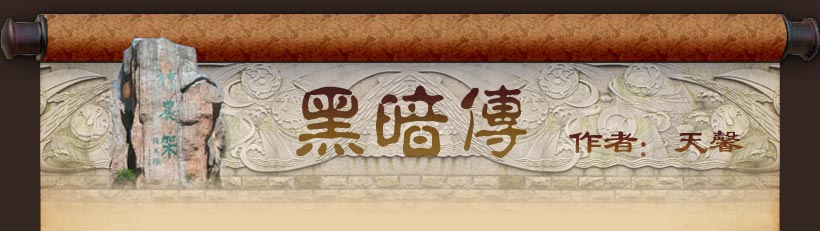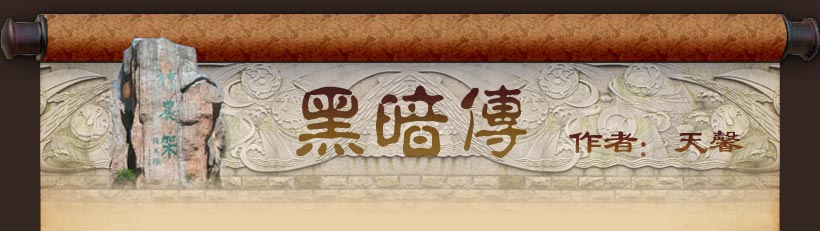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学艺术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儒道两家思想。挂一漏万,叙述如下:以诗教理论为代表的儒家文学观,赋予了中国文学以强烈的道德性格。孔子的 “兴观群怨”说以及他那一言以蔽之的“思无邪”的定论,是将诗的功能与道德完全联系在一起的。韩愈所说的“文以载道”也是强调文学与道德的合一。文学的最 终归宿在于调节现实的人伦关系,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而这些又是获致天人合一境界的初阶。中国古代文学,无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在内容上的最大特征是偏重于政治主题和伦理主题。这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道德性格所决定的。国家兴亡、战争成败、民生苦乐、宦海沉浮、人生聚散、纲常序乱、伦理向背等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基本母题。尤其是有关忠君、报国、爱民等题材更能得到社会的首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佳篇亦往往能传颂千古。爱情、家庭、个人则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居于次要地位。中国文学评论中也从不以纯情文学为上品。至于纯粹的娱乐与休闲作品,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更属少见。
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反对个人情志的宣泄过于偏激,这也充满着理性主义色彩。中国文学之写意抒情,最具温柔敦厚之气。它含蓄、委婉,要求情感的表露合理而有节制,做到孔子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达到中和之美。《诗经•关雎》写男女爱情,哀则寤寐反侧,乐则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然后戛然而止,哀不致蚀骨,乐不致放纵。中国的“怨”诗,往往是怨而不怒,发乎情止乎礼义,鲜有怨刺过火者。如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写被迫离异的爱情悲剧,有“一怀愁绪,几年离索”的悲凉,有“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的隐痛,然终究只是以“莫莫莫”之节制作罢。它有哀伤幽怨之情而无离经叛道之举。再如《古诗十九首》中,写怨妇思夫,思而不得,遂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来自勉自宽。中国文学的这一中庸和平性,不仅由儒家的诗教原则所决定,也由道家“至乐无乐”等观念所支撑,因而历来被视为文学的正宗。中国的古典悲剧,无论叫人如何撕心裂肺,最终或有清官 廉吏的为民伸冤,或有仙境梦中的团圆结局。这正如王国维所说: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
儒家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要有伟大的作品,须先有伟大的人格。这就造成文学与人格合一的特征。中国文学理论认为,作家的气质、才性、情操等决定着作品的风格和成就。正如《文心雕龙•体性》篇所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各师成心,其面如异。”而“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 等等,都说明了文如其人的文学观。
道家的生活理想和人生态度与儒家不同。它主张超脱世俗而与自然为一。这与文学不受外界强力羁绊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因而促進了中国文学独立品格的形成。道家老庄,反对人为,强调自然无为,追求飘逸、神奇,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浓厚的奇幻色彩。
道家对“言意关系”的论述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追求言外之意,讲究意境塑造的优良传统。庄子在《外物》篇中说道:“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庄子认为内在体验只属于心灵而不属于语言,所谓 “无言而心说(悦)”(《天运》),“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道家对语言的深刻理解和追求“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的境界为后来陶渊明等诗人继承。他们不重视华丽的语言,而是在意境塑造和传达弦外之音上用力,形成了中国诗歌、散文独有的风格韵味.因而中国文学艺术在表现技巧方面的最大特色,是极其重视以虚写实,以动写静或以静写动,讲求以少胜多,以无声胜有声,讲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中国文学艺术深受道家“大制不割”、“道法自然”思想的影响,认为天地万物的自然美才是真美。因而艺术创作要力求浑然天成,达到自然之美的最高境界。它反对人为的娇揉造作,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制造人为的晦涩、浮摩、怪诞,崇尚真淳、质朴、清新。刘勰把“自然”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要求。李白曾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赞美自然的艺术风格。苏轼亦极力主张“文理自然,姿态横生”。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历来被尊为自然平淡风格的典范。后人评价陶诗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谈到中国戏剧的佳处时,以一言蔽之:“自然而已。” 并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着于元曲”。中国文学艺术所崇尚的自然美,是大巧之后的返朴。它并非否定人工、技巧,恰恰相反,它要求艺术家有“功参造化”、“巧夺天工”的功力,通过刻苦的技巧训练达到不露刀斧之痕的高超境界─“无技巧”境界。宋代王安石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可以说道出了中国历代艺术家们终身不舍的艺术追求。道家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出现,给中国文学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庄重和沉重之外,增加了些许灵动和灵气。山水文学中的道,表现了对天人合一境界,隐逸与仙境的向往与追求。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苏轼的“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无不透露出道家与自然冥合思想的印记。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的勃兴更是道家思想结出的硕果。“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其间更见悠然忘俗的道家逍遥本色。
道家的“虚静”思想影响了人们观对文学创作规律的理解。历代文学家在谈到生活体验、艺术构思时,都曾把“虚静”说直接引入创作心境的理论中,强调人的心境只有在虚静的状态中才能领悟到天地万物之美,从而感发起兴,诗情勃发。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伫中枢以玄览”,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都是强调道家虚静思想的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